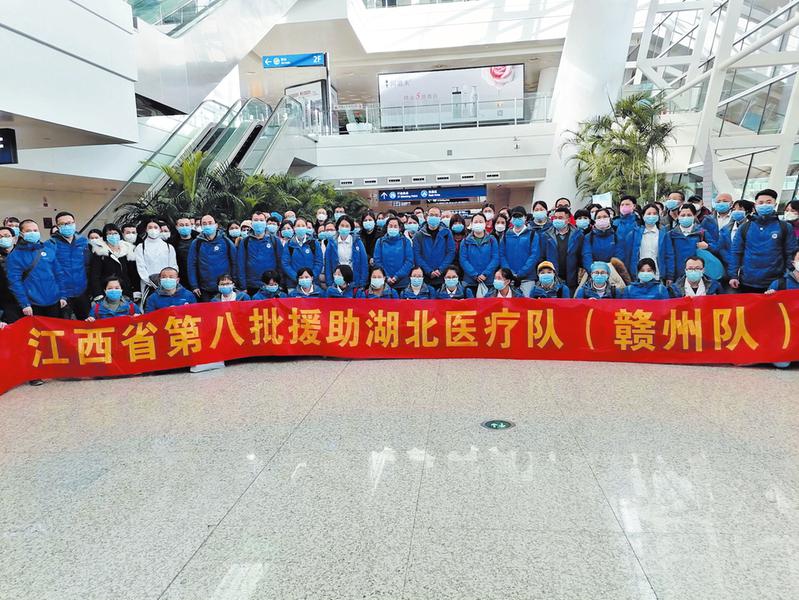从随州叶家山到擂鼓墩 曾随的兴衰沉浮
从随州叶家山到擂鼓墩,空间距离不过二十公里,而时间距离却跨过了六百年。按学界“曾随合一”的主流观点,这一时期,正是西周东周王朝风云急剧变幻、曾随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时期。透过历史典籍和地下文物传出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曾随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这一特征,或许已成为随州人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
A 强楚称王 曾随何去何从
曾随与楚,都是西周初受周王朝分封的封国。曾随封为侯,而楚封为子,“公侯伯子男”,曾随的待遇,要高出楚几个级别。
曾随以姬姓宗室至亲封于汉水之阳,而“汉东之国,随为大”,在周王朝灭鄂而并有其地之后,国力强盛,其势力影响范围包括今汉水以东,桐柏山以南,广水以西,钟祥、京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对于周王朝,作为同宗臣子,曾随坚守南疆;对于“汉阳诸姬”,作为“老大哥”,曾随“亲兄弟之国”,抵御侵略。
相对于曾随的“守”,楚却采取了“攻”。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说,楚国的扩张,是春秋历史上的重要关目。
清代高士奇作《左传纪事本末》:“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若楚矣。”
楚本来被周成王分封于丹淅之地,建都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建立了楚国,但“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
但随着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周王朝势力衰落,楚采取了凌厉的攻势,大肆扩张,即使是同祖同宗的小国,也不放过。如罗国,是夏商时代芈姓部落的一个分支,和楚同祖。商周时代,随楚几经迁徙,到了春秋初期,却被楚所灭,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来又迁至湖南汩罗。
《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所记的 “楚武王侵随”,就是楚国南下扩张的必然选择,对于“汉东”这一南下路上的障碍,是志在必得。
但楚的胃口,却不仅仅是“侵随”,而是“称王”。
就在这侵随、兵临城下的同时,楚对随侯提出了“请王室尊吾号”的要求。
太史公在《史记·楚世家》中,描绘了楚子熊通对随侯说话的神态——
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熊通的神态相当骄横,摆出了一副“我是蛮夷我怕谁”的架式;理由也相当充足——“诸侯皆为叛相侵”,潜台词是“别人做得我也做得”;底气当然是自己拥有 “敝甲”——熊通小玩儿了一下自谦,你可不要被蒙蔽了,那可是相当生猛的楚军!于是提出要求,你随侯不是周天子的本家么,我可以凭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周天子尊奉我的名号,提高我的级别待遇。大军压境,随人不得不替他到周都洛阳,向王室请求尊号,但王室不答应,只好再回来告诉楚。熊通闻讯大怒:“我的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师,很早死去。周成王提拔我的先公,竟只赐予子男爵位的田地,让他住在楚地,蛮夷部族都顺服,可是周王不加封爵位,我只好自称尊号了!”
熊通自立为 “武王”,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自此,楚君皆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此时周室衰微,无可奈何。“随师败绩”,但因实力尚存,影响仍在,而未致灭国之灾,但也不得不订立尊楚为王之“盟”了。
B 卫周抗楚曾随前赴后继
虽与楚订下了尊楚的城下之盟,但曾随并不甘心于做楚的附庸,而牢记着作为周王朝南疆重镇的使命。
就在熊通自称楚武王之后的三年,《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随国准备与郧、绞、州、寥合力“伐楚师”,结果楚军迅速打败郧师,维持了“尊楚”的盟约。
曾随一边顶住楚的压力,坚持抗争,同时,也受到周王朝的责备。《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公元前690年,周庄王召来随国国君,责备其不该尊楚为王。
结果当然是随国“叛楚”,但很快就招来了楚武王的报复。《史记·楚世家》记载较为简略:“楚怒,以随背己,伐随。”而《左传·庄公四年》则较详: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王遂行,卒于賩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蟟,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楚武王死在“伐随”的途中,对于随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一次难得的获胜机会。但楚武王手下对武王之死秘不发丧、虚张声势,兵临随都之下,摆出一个大举进攻的架式,达到了迫使随国与之结盟的目的。
武王之死,并没有中断楚国的扩张进程。
其后的楚成王熊恽是楚武王之孙、楚文王少子。公元前672年,其兄楚王杜敖欲杀他,他逃命到随国,并“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在其危急关头,随国能够帮助熊恽政变夺权,看来当时的随国还是有相当的实力。
楚成王即位后,以“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派人向周天子进贡,以至于周天子赏赐给他祭祀用的肉,并委任他 “镇尔南方夷越之乱”,只是不要侵扰中原。
拿到周天子尚方宝剑的楚成王,王位已稳,师出有名,更加快了扩张的步伐,先后灭贰、谷、绞、弦、黄、英、蒋、道、柏、房、轸、夔等国,至“楚地千里”。
疆域扩大,实力增强之后,楚成王积极投身于中原争霸。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当时称霸的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以楚国未向周天子进贡为由进行讨伐,而楚毫不示弱。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齐国大臣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国力渐衰,而楚国却后来居上,咄咄逼人。而后来的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竟然“问鼎小大轻重”,并狂妄地对王孙满说:你不要以为你的九鼎有多了不起,我的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儿,就足够铸成九鼎了!
“天子九鼎”,而视之如儿戏,楚庄王此语,大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了。而“问鼎中原”一语,便带着雄心、野心和霸气,流传了下来。
而当时,这便是曾随的生存环境。但在如此强悍的楚国面前,曾随又一次举起了“叛楚”的大旗。
公元前640年,据《左传·僖公二十年》所载,“随以汉东诸侯叛楚”,此时为楚成王三十二年,即距离随国帮助成王夺取王位已过了三十二年。面对如日中天、锋头正健的强楚,随国为什么要带领兄弟们进行反抗?是随楚的友好关系发生变化,已经不堪楚国的欺凌?还是为了道义、为了正统、为了维护姬周王朝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些疑问的答案,史籍无载,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但随国此次“叛楚”的结局是没有疑问的,楚又是派大军“伐随”,并“取成而还”,以随的战败认输收场。好在随并未遭灭国之灾,大概是楚成王还念记着随国救命夺位之恩,抑或是因随国实力尚存,有着灭之不如服之的政治考量。
C图存求变 曾随保护楚王
“昭王奔随”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对于随国、楚国,都是一件关系国运走向的大事。
公元前506年,离“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又过去了134年。《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年,吴、楚爆发大战。
吴王阖闾任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伍子胥,并联合唐、蔡二国,奇兵突袭,楚军节节败退。这年冬天,两军决战于柏举(一说在今麻城,一说在今安陆),楚军大败,吴军进逼楚之郢都。
楚昭王一家及随从弃都避难,几死一生,逃到随国。
吴王率军追来,并对随国人说:周王室的姬姓子孙,凡是封在汉水一带的,楚国都把他们灭掉了。现在上天显示天意,要惩罚楚国,而贵君却把楚君隐藏了起来,周王室哪里得罪了你们?贵君如果要报答周王室,就希望能帮助我执行上天的意志,如果这样,就是贵君的恩惠了。汉水以北的土地,都可以归贵君所有。
这番话,吴王说得有情、有理、有利。
随国本为周王朝姬姓子孙,如今周天子有名无实,众多“汉阳诸姬”被楚人所灭,如向吴王交出楚王,即报周王室同宗之恩,又报 “诸姬”被灭之恨,还能光复 “汉阳”故地——吴王的话显然极具诱惑力。
而同时,楚人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公子子期长得酷似昭王,他打算让昭王逃跑,自己穿上他的衣服,说:“把我交给吴军的话,国君就一定能免于被俘。”
面对吴人的诱惑与楚人的打算,随国内部大概争议极大。于是进行占卜,结果是将子期送给吴人“不吉”。随人于是对吴人说:以随国的偏僻狭小而紧挨着楚国,楚国确实保存了我们,而且两国世世代代都有盟誓,至今没有改变。如果有了危难就抛弃别人,又怎么能事奉贵君!贵君的忧患并不只是楚王一人,如果你们征服并安定整个楚国,那么我们就听从你们的命令。
随人占卜的结果,是天意还是人为,不得而知。但吴军大兵压境,作出风险极大的拒绝吴王的决断,还是有着不同以往的政治考量,和很大的勇气。周王室徒有虚名,几乎沦落等同为一个小国,绝无起死回生的可能,再同随之先君一样卫周抗楚,已经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楚灭了,还有吴、还有越……个个都是虎狼之师。不背盟誓、难而不弃,随人答复吴人的一段话,不仅仅是外交辞令,也体现了随国重诺守信的生存与立足的法则。《史记·楚世家》述及此处,还有几句话:“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随人不交出楚王,吴人要自己搜寻。一句“随不听”,更是显示了随人的坚决态度。而吴“罢去”的原因,或许是觉得随人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也或许是碍于随国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不愿扩大战争的规模。
而楚昭王的感动,《左传》中也写得惊心动魄:“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割破胸前之肉,滴血为盟,这是极为神圣庄严的仪式。
楚昭王在随国住了将近一年,吴师退走之后,昭王才回到郢都。后人将他住过的地方称“楚昭王城”。清同治《随州志》引《史记正义》说,“楚昭王城在随州随县北七里。”据文物部门1957年普查,认为楚昭王城在今北郊星光村“荒草子遗址”。
至公元前489年楚昭王去世,他又在位十七年。
而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镼钟,时间为公元前433年。
公元前407年,楚声王娶曾姬无恤为夫人,说明此时随楚关系仍很融洽。
1981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地位相当于国君一级,考古界定在战国中期前段,表明此时曾随尚存……
在风云急剧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曾随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其国运的延续,使我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外,看到了道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
名城保护大家谈
网友“铁心之友”:随州历史文化渊源流长。炎帝神农,开启中华文明之先河;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青铜铸造术、音乐乐理和演奏,开世界音乐之先河;季梁,伟大的思想家,重信尚德;历代先贤,不胜枚举。
市民佳佳:随州悠久厚重的历史确实令人骄傲,令人自豪。但也要清醒认识到随州地域文化也有其局限性。北宋文学家曾巩在《尹公亭记》中指出“随为州,去京师远,其地僻绝”。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很容易导致人们思想的相对保守。对此,当今随州人要更加自觉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抓住发展机遇,创造随州更加美好的明天。
Notice: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is site is submitted, published, edited and uploaded by netizens. This site only provides an exchange platform for such works,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pyright. If you find any works on the website that infringe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 will modify or delete them in a timely manner.